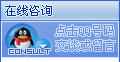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�ɉ��ւ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Ǯ�(d��ng)���Ɏ�Ⱥ�w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̫���͡����x�͡��ɏ�(f��)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ȑ�(y��ng)ԓ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ƃ�(n��i)���족���ஔ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څs���x���w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?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w�ơ���߅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r�£��`����ɵ��ˑ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Լ��ķ��Ķ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ك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ؔ(c��i)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ߞ鿡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^Ҳ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Ї�(gu��)�˶��Ǻ�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o�Լ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Ɏ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ƫƫ��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�Ҋ(ji��n)�L(f��ng)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Ȼ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߷�Ժ��˾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Ɏ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˵ķ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(j��)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κ����ﶼ�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^Ҳ�ͳ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�ᘌ�(du��)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Ӌ(j��)�ģ����m��đС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߃�����͵�I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��ɑ��P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؝��ڷ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׃��һ���ò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Ҷ��Թ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}�ǡ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l(sh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猍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؈�(zh��)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C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ڷ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A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η�ֹ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߹���(qu��n)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��ڽ�¶�Ϳ��h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θĸ���ʮ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ǣ����ԵĈ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(hu��)�Ԅ�(d��ng)�S�o(h��)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牺���²����Ѷ���֮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Ǟ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ǡǡ�����ù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һ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Ӿͮ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y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Ĉ�(zh��)���߲���(hu��)�Ԅ�(d��ng)���ƹ���(qu��n)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ı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溦�º͈�(zh��)��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ƈ�(zh��)���`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ƶȏU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߀���l(shu��)�ܞ��Ї�(gu��)֧�����δ�B�أ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sƫƫ�o(w��)��֧�η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ܷ���ȱλ�ķ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(hu��)�ġ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О�ģʽ��(du��)�ڂ�(g��)�˿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Ǻ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ڂ�(g��)�˘�(g��u)�ɵļ��w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s�Ƿ����Եģ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ÿ��(g��)�ˁ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Ҳ�Ƿ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Ԓ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s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(du��)ÿ��(g��)�ˁ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ܡ����ԡ���һ�N�О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Y(ji��)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Ҳ��ԓ���ܷ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V�o(j��)�U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䪚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˵ķ�ʽ���҂�չʾ���Ɏ���ġ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η��·�(gu��)�ң��Ɏ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ɹ�ͬ�w������Ҫ�M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ǾS�o(h��)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Ă�(g��)��(gu��)�ҿ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o(j��)�ط����Ɏ�Ⱥ�wȱλ�ĭh(hu��n)���³ɾ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鷨���?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Ҫ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ˁ�(l��i)���d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ƶȺ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ć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籾����δ��ɷ��ɹ�ͬ�w�Ľ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ⲿ����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ИI(y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ʢ�У����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ġ��ӎ��(q��)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Ȼ�ɞ�څ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I(y��)���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_(k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Ӹ���ֱ�Է��ϵ��Ɏ��t���ǡ��Բ��˶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δ�B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o(w��)��֧�εĿ��И��w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_��(sh��)�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Ļ���߉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΅s���܆ο����ԡ���һȺ�](m��i)�Г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֪����e�˱�܇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^(q��)һλ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˵IJ�и��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A�õ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Ժԭ��Ҳ�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Q��(sh��)��ҪԺ�L(zh��ng)�w�²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ڷ�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׃�ɷ��ق�(g��)�˺��־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߀�з��و�(ji��n)�ּ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ϵ����Lj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Ժ�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w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еķ���һ�㶼�](m��i)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ķ��لtΨΨ�Z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 (t��ng)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ּ�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���骚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(m��n)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ӏ�(qi��ng)���һ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λ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е��Ɏ�ͬ�ӡ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ܱ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ԡ��Ɏ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u�Ӻ��Ч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^(gu��)�ڷ����Ɏ����w���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9������둗�ķ��·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Εr(sh��)���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T(m��n)ǰѩ���ĪM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܇(ch��)���ăe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ע���ɞ鲻�R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ۮ�(d��ng)܇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ü��X�£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Ч�¡����ɏ�(f��)�ƵĹª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ĪM�x���Ԅ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Ǟ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h(yu��n)���ԣ���(d��ng)�҂��@Ⱥ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ı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�|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Є�(d��ng)��䌍(sh��)ֻҪ�҂�ÿ��(g��)�˶�����ôһ�c(di��n)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͛](m��i)�б�Ҫ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ǘ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](m��i)�б�Ҫ����ô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Լ��ķ��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õ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?zh��)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�ŭ��ԹҲ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Ք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Щ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Ⱥ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η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@�ӵġ��ɉ��ւb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һȺ�](m��i)�Г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@��֮�B(ni��o)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Ȳ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䂀(g��)�ˠ���Ҳ���ܳɞ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˼��wų���ľ��H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ǡ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w��͓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ÿ��(g��)�˶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挦(du��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Ɏ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٣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ߵ���(g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y�ġ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