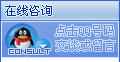|
1978ДкЈ¬°І»ХРЎҚҸҙеҶў„У(dЁ°ng)БЛЦРҮш(guЁ®)Юr(nЁ®ng)ҙеёДёп���ЎЈОеДкЦ®ғИ(nЁЁi)����Ј¬ФЪЦРСлҙуБҰНЖҸVПВ�����Ј¬РЎҚҸҙеГсөД°ь®a(chЁЈn)өҪ‘фіЙһйпL(fЁҘng)ГТИ«Үш(guЁ®)ёчөШөДЎ°јТНҘВ“(liЁўn)®a(chЁЈn)іР°ьШҹ(zЁҰ)ИОЦЖЎұ�����ЎЈКВәуҝҙҒн(lЁўi)�����Ј¬РЎҚҸДЈКҪЖдҢҚ(shЁӘ)КЗЦРҮш(guЁ®)өДТ»ҙОөШ·ҪЦЖ¶ИФҮтһ(yЁӨn)ЎЈ°ь®a(chЁЈn)өҪ‘фӘqИзТ»оwЛА¶шҸН(fЁҙ)ЙъөДРВГз�����Ј¬ЦұҪУМф‘р(zhЁӨn)БЛҪыеd”ө(shЁҙ)ғ|Юr(nЁ®ng)ГсөДЎ°ИЛГс№«ЙзЎұЦЖ¶И��ЎЈғЙ·NЦЖ¶ИҢҰ(duЁ¬)үҫөДҪY(jiЁҰ)№ыёЯПВБўТҠ(jiЁӨn)�Ј¬ҹo(wЁІ)Х“ҸДЮr(nЁ®ng)ГсөД“нЧo(hЁҙ)іМ¶ИЎўЙъ®a(chЁЈn)·eҳOРФЯҖКЗЙз•ю(huЁ¬)Р§ТжҒн(lЁўi)ҝҙ��Ј¬РЎҚҸДЈКҪ¶јҙу«@И«„Щ�Ј»Ў°ИЛГс№«ЙзЎұКЈПВәУДПДПҪЦҙеөИБИБИҹo(wЁІ)ҺЧөДЎ°ЯzАПЯzЙЩЎұЈ¬ТІЦ»КЗҝҝЦРСлЭ”СӘІЕөГТФҫSіЦМ“јЩ·ұҳs����ЎЈРЎҚҸҙеөДҶўКҫФЪУЪЈ¬Ц»ТӘҫSіЦ»щұҫ№«ЖҪәНЧФУЙөД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ЦИРт���Ј¬өШ·ҪФҮтһ(yЁӨn)НщНщДЬ®a(chЁЈn)ЙъЧоәГөДЦЖ¶И����ЎЈКВҢҚ(shЁӘ)ЙП�����Ј¬ёчөШ¶јҝЙТФНЖіцЧФјәХJ(rЁЁn)һйЧоәГөДЦЖ¶И����Ј¬ҸД¶шФЪИ«Үш(guЁ®)·¶ҮъғИ(nЁЁi)РОіЙТ»ӮҖ(gЁЁ)Ў°ЦЖ¶ИКРҲц(chЁЈng)ЎұЎЈЖ©ИзЦШ‘cҝЙТФНЖіцЎ°ЦШ‘cДЈКҪЎұ�Ј¬ҸV–|ҝЙТФНЖіцЎ°ҸV–|ДЈКҪЎұЈ¬¶шҫҝҫ№ДДӮҖ(gЁЁ)ёьәГ���Ј¬РиТӘФЪТ»ӮҖ(gЁЁ)№«ЖҪ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өДӯh(huЁўn)ҫіПВУЙИ«Үш(guЁ®)ИЛГсҒн(lЁўi)Фu(pЁӘng)ғr(jiЁӨ)�ЎЈҫНәНЙМЖ·КРҲц(chЁЈng)УРДЬБҰ’юЯxРФғr(jiЁӨ)ұИЧоёЯөДЙМЖ·Т»ҳУ���Ј¬ЦЖ¶ИКРҲц(chЁЈng)ТІУРҙуАЛМФЙіөДДЬБҰ�Ј¬°СүДЦЖ¶ИМФМӯөф��Ј¬°СәГЦЖ¶ИБфПВҒн(lЁўi)����ЎЈ
И»¶шЈ¬ТӘЧҢЦЖ¶ИКРҲц(chЁЈng)ХжХэ°l(fЁЎ)“]ЧчУГ����Ј¬Үш(guЁ®)јТЦЖ¶ИҝтјЬұҫЙнұШнҡ·ыәПИэӮҖ(gЁЁ)—lјю��ЎЈКЧПИ�Ј¬ұШнҡҸVй_(kЁЎi)СФВ·���Ј¬ІўҸДЦЖ¶ИЙПұЈЧC‘—·ЁөЪ35—lТҺ(guЁ©)¶ЁөДСФХ“ЧФУЙ���ЎЈөШ·ҪДЈКҪөД№«ЖҪ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ТвО¶Цш№«ХэФu(pЁӘng)ғr(jiЁӨ)Ј¬¶ш№«ХэФu(pЁӘng)ғr(jiЁӨ)КЧПИКЗҪЁБўФЪ»щұҫЦӘЗйөД»щөA(chЁі)ЙП���ЎЈИз№ыЯBөШ·ҪДЈКҪөДХжҢҚ(shЁӘ)Р§№ы¶јІ»ЦӘөА���Ј¬Х„әО№«ХэФu(pЁӘng)ғr(jiЁӨ)ЈҝЦШ‘cЎ°іӘјtҙтәЪЎұТФҒн(lЁўi)����Ј¬ЦШ‘cКРГсЛЖәхҹбЗйёЯ°әЈ¬УРөД·ЁҢW(xuЁҰ)јТ“ю(jЁҙ)ҙЛФu(pЁӘng)Х“Ў°ИЛГсТІ•ю(huЁ¬)үҷВдЎұ���ЎЈЧчһйҙуҪЦЙПөДЖХНЁДРЕ®����Ј¬ИЛГс®”(dЁЎng)И»ҝЙДЬЎ°үҷВдЎұ�����Ј¬Ҷ–(wЁЁn)о}ФЪУЪИЛГсһйКІГҙ•ю(huЁ¬)үҷВд��Јҝҫҝҫ№КЗКІГҙФміЙЛыӮғүҷВд��ЈҝФЪЦШ‘cИЛГсҙ©ЦшҢЈйT(mЁҰn)ЦЖЧчөДЦЖ·юЕdёЯІЙБТЎ°іӘјtЎұөД•r(shЁӘ)әт�Ј¬ЛыӮғКЗ·сЦӘөАЧФјәһйҙЛё¶іцөДҙъғr(jiЁӨ)Јҝ®”(dЁЎng)И«Үш(guЁ®)І»ЙЩИЛһйАоЗf°ёЎ°ҙтәЪЎұәИІКөД•r(shЁӘ)әт�����Ј¬ЛыӮғКЗ·сЦӘөА·ЁНҘҢҸЕРұіәуөДЎ°ғИ(nЁЁi)Д»Ўұ��ЈҝИз№ыИЛГсЦ»КЗТ»ИәЎ°І»ГчХжПаөДИәұҠЎұ���Ј¬ДЗГҙЛыӮғ»щУЪМ“јЩРЕПўЧціцөДЕР”аұШИ»КЗЕӨЗъөД���ЎўЎ°үҷВдЎұөДЎўЎ°лxЧVЎұөД����Ј¬ө«КЗҶ–(wЁЁn)о}өДёщұҫп@И»І»ФЪУЪЎ°ИЛГсЎұЈ¬¶шФЪУЪІ»ЧҢИЛГсЦӘөАХжПаөДЦЖ¶И����ЎЈТтҙЛ��Ј¬ТӘРОіЙөШ·ҪДЈКҪөД№«ЖҪ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����Ј¬Хюё®КЧПИІ»өГүәЦЖ�����ЎўҝШЦЖ»тЕӨЗъСФХ“����Ј¬ҫНәНХюё®І»өГНЁЯ^(guЁ°)ЦёБоёЙоA(yЁҙ)КРҲц(chЁЈng)ЎўұЈЧo(hЁҙ)ДіР©ЖуҳI(yЁЁ)����ЎўЖзТ•ЖдЛьЖуҳI(yЁЁ)Т»ҳУЈ¬·с„tЛщЦ^өДЎ°КРҲц(chЁЈng)ЎұұШИ»КЗЧғПаөДҮш(guЁ®)јТүЕ”а�ЎЈ
ЖдҙОЈ¬ФЪСФХ“ЧФУЙәН»щұҫЦӘЗйөД»щөA(chЁі)ЙП���Ј¬ИЛГс‘Ә(yЁ©ng)ұ»ЩxУиЧФУЙЯx“сөДҷа(quЁўn)Аы��Ј¬УИЖдКЗНЁЯ^(guЁ°)‘—·ЁөЪ34—lТҺ(guЁ©)¶ЁөДЯxЕeҷа(quЁўn)ҙЩК№өШ·ҪДЈКҪЯx“с·ыәПөШ·Ҫ¶а”ө(shЁҙ)ГсТв��ЎЈјЩИзЎ°ЦШ‘cДЈКҪЎұҢҚ(shЁӘ)РРід·ЦөДРЕПў№«й_(kЁЎi)�����Ј¬УИЖдКЗШ”(cЁўi)ХюЕcЛҫ·ЁРЕПў№«й_(kЁЎi)����Ј¬ЦШ‘cКРГсФЪЦӘөАЧФјәөДё¶іцІўЧціцҷC(jЁ©)•ю(huЁ¬)іЙұҫЕР”аЈЁЖ©ИзЦЖЧчЦЖ·юөДҪӣ(jЁ©ng)ЩM(fЁЁi)ҝЙТФУГУЪбt(yЁ©)Ҝҹ��ЎўЙзұ���Ј»тБx„Х(wЁҙ)ҪМУэЈ©Ц®әу�Ј¬ИФИ»“нЧo(hЁҙ)Ў°іӘјtҙтәЪЎұөД¬F(xiЁӨn)УРДЈКҪ�����Ј¬ДЗГҙЯ@НкИ«КЗЛыӮғөДЧФЦчӣQ¶Ёҷа(quЁўn)���ЎЈ®”(dЁЎng)И»����Ј¬Из№ыЎ°іӘјtЎұЩM(fЁЁi)УГЖдҢҚ(shЁӘ)КЗҒн(lЁўi)ЧФУЪЦРСлДіІҝөДЮD(zhuЁЈn)ТЖЦ§ё¶��Ј¬ЦШ‘cКРГсҢҚ(shЁӘ)лHЙПКЗФЪІ»Таҳ·(lЁЁ)әхөШ»ЁИ«Үш(guЁ®)ИЛГсөДеXЈ¬ДЗГҙИ«Үш(guЁ®)ёчөШөДј{¶җИЛ¶јУРұШТӘ·ҙЛјЯ@·NДЈКҪөДәПАнРФ����ЎЈКВҢҚ(shЁӘ)ЙПЈ¬УЙУЪөШ·ҪДЈКҪКЧПИҢҰ(duЁ¬)өШ·ҪИЛГс®a(chЁЈn)Йъәу№ы�Ј¬Тт¶шФЪҪ^ҙу¶а”ө(shЁҙ)ЗйӣrПВөШ·ҪЎ°ИЛГсөДСЫҫҰКЗС©ББЎұөДЈ¬НкИ«ҝЙТФҢҰ(duЁ¬)®”(dЁЎng)?shЁҙ)ШҢ?shЁӘ)РРөДХюІЯЧціцГчЦЗЕР”а�����ЎЈИз№ыөШ·ҪЯxГсұ»ЩxУиЧФЦчӣQ¶Ёҷа(quЁўn)�Ј¬ДЗГҙФS¶аөШ·ҪЮr(nЁ®ng)ГсЎ°ұ»ЙПҳЗЎұөИЧғПа„ғҠZЮr(nЁ®ng)Гсҷа(quЁўn)АыөДНБөШЦЖ¶ИЎ°ёДёпЎұёщұҫІ»ҝЙДЬҙжФЪЈ»Ц»ТӘ¶а”ө(shЁҙ)Юr(nЁ®ng)ГсөДЯxЕeҷа(quЁўn)әН°l(fЁЎ)СФҷа(quЁўn)ҢҰ(duЁ¬)®”(dЁЎng)?shЁҙ)Ш№ЩҶT°l(fЁЎ)“]Т»ьc(diЁЈn)ЧчУГ�����Ј¬ҫНӣ](mЁҰi)УРИЛёТ№«И»ЦЖ¶ЁЗЦ·ёЮr(nЁ®ng)ГсАыТжөДХюІЯ�����Ј¬ёьІ»УГХf(shuЁӯ)ФЪИ«Үш(guЁ®)ёчөШОөИ»іЙпL(fЁҘng)�����ЎЈПа·ҙЈ¬УРҝЪҪФұ®өДЎ°іЙ¶јДЈКҪЎұ„tІ»ғH•ю(huЁ¬)КЬөҪ®”(dЁЎng)?shЁҙ)ШЮr(nЁ®ng)ГсөДҸҠ(qiЁўng)БТ“нЧo(hЁҙ)����Ј¬¶шЗТТІ•ю(huЁ¬)ЧФ„У(dЁ°ng)өГөҪёчөШјҠјҠР§·ВЎЈ
Чоәу��Ј¬өШ·ҪЦЖ¶И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ЯҖРиТӘФЪ»щұҫ№«ХэЕc·ЁЦОөДЦИРтПВХ№й_(kЁЎi)�����ЎЈУРР©өШ·ҪёДёплmИ»ФцЯM(jЁ¬n)БЛ¶а”ө(shЁҙ)ИЛГсөДАыТж�Ј¬…sҝЙДЬЗЦ·ёЙЩ”ө(shЁҙ)ИЛөДәП·Ёҷа(quЁўn)Тж���ЎЈИз№ыёДёпФЪҝӮуwЙПөГҙуУЪК§��Ј¬ЗТӣ](mЁҰi)УРёьәГөДМжҙъДЈКҪ��Ј¬Я@ҳУөДёДёпИФИ»ҝЙТФНЖЯM(jЁ¬n)���Ј¬ө«КЗұШнҡЩxУиТтҙЛ¶шКЬ“pөДИәуwЯm®”(dЁЎng)Сa(bЁі)ҫИЈ¬ФКФSЛыӮғНЁЯ^(guЁ°)·ЁВЙҷC(jЁ©)ЦЖҫSЧo(hЁҙ)ЧФјәөДҷа(quЁўn)Аы�����ЎЈТ»ӮҖ(gЁЁ)Н»іцөДАэЧУКЗЮr(nЁ®ng)ҙеіЗКР»ҜұШнҡҪЁБўФЪГсЦчәН·ЁЦО»щөA(chЁі)ЙПЈ¬ЩxУиК§өШЮr(nЁ®ng)Гс№«Хэ¶шід·ЦөДСa(bЁі)ғ”��Ј¬ЧҢЛыӮғ№«ЖҪ·ЦПн°l(fЁЎ)Х№өДіЙ№ы����Ј¬ЦБЙЩЧцөҪИОәОИЛөД»щұҫЙъУӢ(jЁ¬)І»•ю(huЁ¬)Тт?yЁӨn)йЎ°°l(fЁЎ)Х№Ўұ¶шКЬөҪ“pәҰЎЈИз№ыДЬЧцөҪЯ@Т»ьc(diЁЈn)���Ј¬И«Үш(guЁ®)ёчөШөДЎ°СӘІрЎұ�ЎўЙПФLДЛЦБұ©БҰӣ_Н»ҢўЧФ„У(dЁ°ng)ПыК§����Ј¬ЦРҮш(guЁ®)өДЮr(nЁ®ng)ҙеёДёпәНіЗКР°l(fЁЎ)Х№ҢўҸДҙЛЧЯЙПАнРФЬүөАЎЈ
Ц»ТӘ·ыәПЧФУЙ�����ЎўГсЦчЕc·ЁЦОөД»щұҫФӯ„t�����Ј¬БјРФөДөШ·ҪЦЖ¶И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ЕcПа»ҘҪииbР§·ВҢўЧФ„У(dЁ°ng)й_(kЁЎi)Х№��Ј¬¶шІ»РиТӘЦРСлЦұҪУіцГжНЖРР��ЎЈҝЙП§өДКЗ���Ј¬УЙУЪІЙИЎЦРСлјҜҷа(quЁўn)ДЈКҪ����Ј¬ПсРЎҚҸҙеЯ@ҳУіЙ№ҰөДЦЖ¶ИФҮтһ(yЁӨn)ФЪЦРҮш(guЁ®)ІўІ»іЈТҠ(jiЁӨn)���ЎЈ®”(dЁЎng)И»��Ј¬ЦРСлТІЗеіюЦӘөА����Ј¬ҢҰ(duЁ¬)УЪЯ@ҳУТ»ӮҖ(gЁЁ)эӢИ»ҙуҮш(guЁ®)�Ј¬І»ҝЙДЬЛщУРХюБо¶јТ»ВЙҒн(lЁўi)ЧФЦРСл����Ј¬·с„tұШИ»»ШөҪУӢ(jЁ¬)„қҪӣ(jЁ©ng)қъ(jЁ¬)өДИf(wЁӨn)сRэRаіҫЦГжЎЈБнНв����Ј¬ФЪҢҚ(shЁӘ)К©Р§№ыОҙЦӘөДЗйӣrПВЈ¬ЩQ(mЁӨo)И»ФЪИ«Үш(guЁ®)НЖРРТ»н—(xiЁӨng)ХюІЯ•ю(huЁ¬)®a(chЁЈn)ЙъҳOҙупL(fЁҘng)лU(xiЁЈn)�����Ј¬Ў°ҙуЬSЯM(jЁ¬n)ЎұФміЙөДұҜ„ЎҝЙЦ^ТуиbІ»Яh(yuЁЈn)ЎЈТтҙЛ�Ј¬ЦРСлФЪЦT¶аоI(lЁ«ng)УтНЖРРЎ°ФҮьc(diЁЈn)ЎұЈ¬ө«КЗЯ@Р©ФҮьc(diЁЈn)Т»°гҫЦПЮУЪјјРg(shЁҙ)ХюІЯҢУГж����Ј¬¶шЗТЦРСлЦёҢ§(dЁЈo)ЧчУГЯ^(guЁ°)ҙуЈ¬өШ·ҪЧФЦч„“(chuЁӨng)РВ„У(dЁ°ng)БҰІ»Чг��ЎЈёьЦШТӘөДКЗ����Ј¬Т»ІҝҶОТ»ЦЖ‘—·ЁНщНщҢҰ(duЁ¬)Йжј°өШ·ҪЧФЦчӣQ¶ЁөДКВТЛТҺ(guЁ©)¶ЁЯ^(guЁ°)¶аЈ¬ҸД¶шКшҝ`өШ·Ҫ„“(chuЁӨng)РВөДКЦД_�����ЎЈлmИ»‘—·ЁөЪ3—lТҺ(guЁ©)¶ЁБЛЎ°ФЪЦРСлөДҪy(tЁҜng)Т»оI(lЁ«ng)Ң§(dЁЈo)ПВ�Ј¬ід·Ц°l(fЁЎ)“]өШ·ҪөДЦч„У(dЁ°ng)РФЎў·eҳOРФөДФӯ„tЎұ�Ј¬ө«КЗІўӣ](mЁҰi)УРТҺ(guЁ©)¶ЁЯm®”(dЁЎng)Ҫз¶ЁЦРСлЕcөШ·ҪВҡДЬөДәПАнҷC(jЁ©)ЦЖЈ¬Тт¶шФЪҢҚ(shЁӘ)Ы`Я^(guЁ°)іМЦРЎ°Ҫy(tЁҜng)Т»оI(lЁ«ng)Ң§(dЁЈo)ЎұНщНщүәө№БЛөШ·ҪЎ°Цч„У(dЁ°ng)РФ�����Ўў·eҳOРФЎұЎЈЖ©ИзФЪЙПТ»ҢГЯxЕeЦР�����Ј¬УРР©өШ·ҪҮLФҮаl(xiЁЎng)жӮ(zhЁЁn)йL(zhЁЈng)ЦұЯxФҮтһ(yЁӨn)���Ј¬Чоәуұ»И«Үш(guЁ®)ИЛҙуҪРНЈ��Ј»ИҘДкЛДҙЁБ_ҪӯҝhҮLФҮИЛҙуҙъұн№ӨЧчКТ����Ј¬ТІәЬҝмКЬөҪЙПјү(jЁӘ)ёЙоA(yЁҙ)���ЎЈ
ЖдҢҚ(shЁӘ)����Ј¬°ҙХХТФЙПИэҙуФӯ„tәвБҝ�����Ј¬Я@Р©өШ·ҪФҮтһ(yЁӨn)Іўҹo(wЁІ)І»НЧЦ®МҺ�Ј¬Тт¶шЙПјү(jЁӘ)ёЙоA(yЁҙ)КЗІ»ұШТӘөД���ЎЈЦРСлРиТӘЧцөДІ»КЗНЁЯ^(guЁ°)РРХюГьБоЦұҪУёЙоA(yЁҙ)�Ј¬¶шЗЎЗЎКЗНЁЯ^(guЁ°)·ЁВЙҷC(jЁ©)ЦЖұЈЧCөШ·ҪФҮтһ(yЁӨn)·ыәПЧФУЙЎўГсЦчЕc·ЁЦОФӯ„t���Ј¬ҸД¶шһйБјРФөДөШ·ҪДЈКҪёӮ(jЁ¬ng) Һ(zhЁҘng)„“(chuЁӨng)ФмІўҫSЧo(hЁҙ)ЦЖ¶Иӯh(huЁўn)ҫі�����ЎЈЦ»УРЯ@ҳУ�����Ј¬ЦРҮш(guЁ®)ёДёпІЕДЬАm(xЁҙ)Ң‘(xiЁ§)РЎҚҸӮчЖж���ЎЈ |